纪念张舜徽先生:君子之于学也,美成在久
人物简介:
张舜徽(1911年7月-1992年11月)湖南沅江县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文献研讨会会长等。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长于校勘、版本、目录、声韵、文字之学。出生于书香世家,自幼由父亲身授业,后又转益多师,从小到大,走的是自学之路。在华中师范大学执教40年之久,曾任中国历史文献研讨会会长,是中国第一位历史文献学博士生导师。一生完成学术著作24部共计八百万字。精于“小学”,博通四部,成为一代“通人”大家。其学术著作全部由毛笔撰写完成。

张舜徽
读张舜徽先生《壮议轩日记》日记有感
张舜徽先生(1911——1992)有写日记的习惯,累月经年,积稿盈箱,而先生一生流离颠沛,大部分日记已经在流浪动乱的岁月里流失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湖南图书馆竟然搜集到了张舜徽先生在湖南和兰州讲习期间的部分日记,先生阅后欣喜异常,宛如重回居湘入陇、讲席四方的壮岁时光,感慨万端,亲为题写《壮议轩日记》,并将日记分为“居湘编”、“入陇编”两部分。《壮议轩日记》起于 1942年9月24日,止于1947年1月7日。因身经战乱流浪,《壮议轩日记》时断时续,或详或略,大致包括了先生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北平民国学院(抗战时迁入湖南)和1946年入陇任教于兰州大学的这一时期的历史。2010年11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张舜徽壮议轩日记》(以下简称《日记》)。
“壮议”一语出自《大戴礼记·曾子立事》:“其少不讽诵,其壮不论议,其老不教导,亦可谓无业之人矣。”“壮议轩”是先生书斋名号,《日记》谓:“余生于辛亥七月。去秋三十已满,盖古人学成之年,而吾碌碌如斯,因取《大戴记》之语,名所居曰‘壮议轩’。以期昕夕省惕,庶几免于无业之讥,非敢高论以忤俗也”(《日记》97页)。1942年11月,先生特地请著名书画家徐绍周先生题写“壮议轩”而“悬之壁间”,以“壮议轩”名其所居,正表现了先生心雄万丈,高标自置,力图有所作为,绝不肯落入庸俗的庞大学术志向。比起先生考论翔实的煌煌学术著作,《日记》娓娓叙说,细致生动,剖白心迹,寓学术于日常生活,于细碎的生活场景中显现先生丰富的心灵世界,因而显得朴素而亲切。作为一代国学大师,张舜徽先生一生托命学术,很少涉猎政治,每日朝披夕吟,手不释卷,心有所得,便记于《日记》。在一定的意义上,先生的《日记》是生活的记录,也是学术的记载,先生后来广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广校雠略》、《清人文集别录》、《郑学丛著》、《周秦道论发微》、《汉书艺文志释例》等在《日记》中已见雏形。先生《日记》以学术为中心,风雅满篇,书香四溢,探索古今,谈论纵横,显示出先生学术思想构成的历史渊源和人生轨迹。尤其是先生《日记》字迹刚毅俊秀,一笔不苟,历时七年,洋洋二十余万言,竟无一处勾画,可谓书法精品,在古今学者的日记中甚为稀有。
一、学者用日记记录一生
《日记》起笔于1942年的中秋节,此时先生刚过而立之年,任教于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为躲避日寇战火,那时的国立师范学院辗转至偏僻的湖南安化县蓝田镇。虽然这里聚集了钱基博、马宗霍、钱钟书、钟泰、骆鸿凯等硕学耆儒,一时间群英聚首,人文荟萃,但总体说来这里生活和学术条件还是相当艰辛的,地域偏僻、道路阻塞、山川荒凉、风气锢塞成了蓝田小镇的写照。小镇的生活是艰辛的,先生《日记》中多处提及生活不易、物价起飞的现实情况。先生讲学蓝田,而寄妻儿于乡里,其间虽然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团聚,但由于“薪桂米珠,居大不易,又不得不早遣之归”,先生是怀着愧疚的心情将妻子儿女送还乡下的:“每自念恩不逮于妻孥,力不周乎俯畜,殊不能恝然于怀。”而这里的学术条件也相当简陋,《日记》记载,1942年10月7日先生去学院图书馆欲借《东都事略》、《续通鉴长编》、《系年要录》、《宰辅编年录》、《三朝北盟会编》诸书而不得,他不由感叹:“居此穷乡,求一常见书而不能得,虽日饫酒食而无以疗饥渴。”而先生的苦痛还远不仅如此,先生正值壮年,英气逼人,且以古为师,不免睥睨今古,目无下尘,因而横遭物议,不见容于同僚,处境颇为困难。先生在1943年3月《日记》中写道:“在此半月中横被口语,使人居之不安,日夜愁悒愤懑。深感世塗险巇,行路殊不易易也。”(《日记》336页)在如此境遇里,先生甚至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自丁丧乱,居此穷山,不徒无书可读,抑亦无人可语,愤愤兀坐,如在囹圄。”(《日记》340页)这也是先生后来分开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移砚陶家湾,任教北平民国学院的重要缘由。而比起个人遭际的苦难,更不幸的是此时整个国家正堕入敌寇入侵的沉重灾难之中。1944年夏,日军长驱直入,大举南侵,长沙、湘潭、湘乡、邵阳等相继失守,先生因“内子怀妊六七月,亦不敢轻言远徙”(《日记》484页),仓促中,只好暂避到宁乡朱石桥一杨姓学生家中。8月13日,日军侵扰先生避难的村中,荒山野岭上“男女千百,呼号啼哭之声闻数里。”先生只好带着即将分娩的妻子和孩子,仓皇奔命——“率妻子,负被帐而行,随乡人以共登天子岭”,蜷伏丛莽中,屏声敛气,不敢耳语,“惟闻枪声时远时近,时断时续。”入夜,露宿山巅,“乡人环坐,以待天明。”而山岭上却密云骤起,阴雨绵绵,凉风袭身,就在逃难后的第二天早晨,遭到惊吓的师母在奔波劳顿中生下了一个女儿。敌人离去后,呈如今先生面前的现象是凄惨的:
待敌退归来,家中荡无余物,徒四壁立耳。吾所藏书数十箱,悉散乱委弃于地。壮者散之四方,啼饥于外;老者遄还故里,号寒于内。(《日记》490页)
在外寇入侵的离乱中,先生内心充满了宏大的悲伤与愤懑,仰望苍天,徒唤奈何:“我生不辰,斯丁厄运,谓之何哉!”(《日记》491页)
读先生的记述离乱中的文字,至今仍人感到神情紧张,心绪难平。外寇入侵,同僚物议,生活贫苦,前途迷茫,这一时期是先生境遇最苦的时期,但却是先生用力最勤、著述最勤的时期,正是在湘南的崇山峻岭中,先生积石采铜,蓄势待发,完成了向一代学术大师的跨越。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日记》中最为感人的就是先生在困难困苦中孜孜矻矻、勤勤恳恳的力学苦读的形象。先生深知学术之困难,如不付出超越常人的努力,永远无法到达学术的顶峰,《日记》中写道:
盖著书之业,谈何容易!必须刊落声华,专注神志,先之以十年廿载伏案之功,再益以旁推广览批检之学,反诸己而有得,然后敢著纸笔。困难寂寞,非文士所能堪。(《日记》441页)
在先生心目中,学术是神圣的、庄严的,因而先生立下了“刊落声华,专注神志”的庞大志向,忍耐着困难寂寞,在经年累月的力学苦读中积累着“十年廿载伏案之功”。1942年农历八月十六日(公历9月25日),先生从学院图书馆借得“孙籀庼、俞曲园书数种假之以归”,当夜“夜阅《籀庼述林》至二鼓后”,第二天就将十卷本的《籀庼述林》阅读完毕。据《日记》记载,从1942年的9月24日始,到1943年1月20日止,在一百余天的时间里,先生阅读的著作有:
1.《籀庼述林》十卷 2.《白华前稿》六十卷 3.《铁桥漫稿》十三卷 4.《春在堂全书》二百五十卷5.《石遗室诗话》三十二卷 6.《南畇文稿》十二卷 7. 《三鱼堂文集》并《外集》十八卷 8.黎劭西《钱玄同先生传》 9.《三鱼堂日记》二卷 10.《谭复堂日记》八卷11.《四库全书提要》二百卷 12.《显志堂稿》十二卷13《铜熨斗斋随笔》八卷14 .《陶文毅公文集》六十四卷15.《逊志堂杂钞》十卷16.《江郑堂隶经文》四卷17.《刘梦涂文集》十卷18.《姚海槎书七种》七十六卷19.《清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 20.《汤潜庵集》二卷21.《国朝文录》八十二卷22.《小仓山房文集》(含续集、外集)四十三卷23.《忠雅棠文集》十二卷24.《汉学师承记》八卷25.《周书斠补》四卷26.《魏鹤山大全集》一百零九卷27.《饴山堂文集》十二卷 28.《巢经巢文集》六卷29.《逸周书》十卷30.《苍莨初集》二十一卷 31.《程侍郎遗集》十卷32.《有恒心斋文集》十一卷33.《养知书屋文集》二十八卷34.《左文襄文集》五卷35.《天岳山馆文钞》四十卷36.《唐确慎公集》十卷37.《曾文正公文集》四卷38.《养晦堂文集》十卷39.《望溪先生文集》(含续集、外集)三十卷40.《大学衍义》四十三卷41.《大戴礼记》之《子张问入官》、《文王官人》(背诵)42.《洪范》、《中庸》诸篇(温习)43《礼运》、《西铭》诸篇(默诵)44.《吕氏春秋》(温习)45.《六家要旨》46.《庄子·内篇》(温习)47.《庄子·胠箧》(温习)48.《与孙豹人书》(默诵)49.《严先生祠堂记》(温习)50.《荀子·劝学》、《礼论》诸篇 (温习)
这个“百天阅读书目”是根据先生《日记》任意截取的,在一百余天里,先生居然阅读了四十多位清代学者的文集,温习了《吕氏春秋》、《庄子》、《礼记》《、大戴礼记》等经典,背诵了《六家要旨》、《礼运》等重要文献,校订了《逸周书》等著作。值得指出的是,除了《清经世文编》、《国朝文录》等卷帙浩繁的著作以外,先生的阅读不是泛泛的浏览,而是“遍加丹黄,从无一字之跳脱”的精读。先生对读过的清人文集都提玄勾要,撮其大略,《清人文集别录》正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在一个战乱年代里,一位中国普通学者在偏僻的湖南深山里的“百日阅读书目”,让我们深深敬佩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即便在学术便利、资讯发达的今天,面对先生的百日阅读书目,我们仍感动不已。
这是先生壮年读书岁月的一段寻常日子,没有特别之处。它不是偶尔,也不是突击,而是晨钟暮鼓中伴青灯黄卷,兀兀恒年从不懒惰的学术坚持。先生治学不急功近利,不刻意求新,不刻意发表倾动一时之言论,而是以坚韧自励,强调积累,强调坚持,显示了从容坚定的学术自信。先生读书的原则是一以贯之的,其《日记》以陆陇其《戒子书》“读书必以精熟为贵”以自警:
欲速是读书人第一大病。功夫只在绵密不间断,不在速也。能不间断,则一日所读虽不多,日积月累,自然充足。若刻刻欲速,则刻刻做潦草功夫,此终身不能成功之道也。(《日记》79页)
先生常以《庄子·人间世》“美成在久”鼓励后学,先生去世前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6期)写下了“美成在久,日进无疆”的贺词,这句话也成了他留给后世的最后格言。与学术上一时间的冲动和热情相比,学术的坚持需要更大的毅力和韧性。从《日记》来看,先生有早晨温习背诵、夜晚阅读写作的习惯,因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日记》中 “晨起默诵”、“读书至二鼓后”的字样,先生是把本人的整个人生拜托于学术事业的,在先生身上我们看到了学术坚持的力量。先生有头痛之疾,《日记》中常常有“头晕身热”、“双手冰寒”之类的记载,而先生却从不因而而辍学,以宏大的毅力忍耐病痛的侵袭和折磨。1943年4月25日的《日记》记载:
早起头痛犹厉,心神亦昏扰不宁,惟静坐瞑目以将息之。友人阮真邻余而居,力劝余爱啬精神,节劳节思。彼盖见余近来用功甚苦,而为是言也。
先生惜时如金,稍有放松,便痛惜不已,常常自责。1946年27日先生早晨起来诵读袁准《正书》,以为“精言胜意,所在皆是,为三復焉。”上午十时有朋友来访,坐谈甚久。中午,有友人招饮,先生“饮酒独多,幸不及乱”。下午,先生以中文系主任身份参加兰州大学的校务委员会,“议事甚多,至点灯时方散。”晚上,学校设宴招待各位与会者。这个在今天看来非常普通的一天,先生却为虚与应付、参与俗务而自责,以为“今日扰于杂事,看书不多,不啻虚抛一昼。因感于酒食论辩,甚妨读书。”(《日记》683页)从仅仅一日的读书不多,先生马上认识到“酒食论辩,甚妨读书”,正由于这样的自警自省,当天晚上“入夜,检览杂书,至三更犹不觉惫”,他是想通过长夜苦读来补偿白天的“看书不多”。值得一提的是,《日记》中如此所谓的“虚抛一昼”,仅此一处,其它一切的时间里先生都在伏案苦读,即便是与人交往,也都是同仁间的商讨揣摩、品艺论学。“少壮工夫老始成”,先生之所以在历史学、文献学、目录学、音韵学、思想史等方面都获得杰出的成就,根本源自于他超乎常人的勤奋和努力。
二、湖南之矿,终待湖南人发掘之
先生将整个生命都交付学术,源于他对学术神圣的真诚信仰。《日记》谓:
暇悟儒家之异于诸子者,总在教人力学。《论语》首章即言“学而时习”,下逮荀卿为《劝学》,扬子《法言》则为《学行》,王符《潜夫论》则为《赞学》,徐干《中论》则为《治学》,此数子者,皆儒家也,开宗明义,无不重学。(《日记》94页)
先生高举儒家重学力行的伟大旗帜,整个生命都浸润和沐浴在传统文化光芒的朗照里。儒家倡导的力学、劝学、赞学、治学、学行,成为先生真实的人生写照。可以看到,《日记》的主体部分,同时也是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先生劝学、论学、学行的学术思想体系。本原的学术根基,识见的学术原则,实用的学术理念,湖湘的学术传统,通人的学术气候——代表了了张舜徽学术思想的根本精神。虽然先生《日记》只是他三十一岁到三十六岁的人生记载,却显示出他的学术思想已经走向真正的成熟,之后,他不断坚持着这样的学术理想,年既老而不渝。
1.“惟根原之地,万不可绝”——本原的学术根基。
时人论及张舜徽先生的学术,恒言先生以通人之学为第一要义,其实,先生虽然倡导会通之学,标举通人气候,而其最为注重的还是学术的本原建设。张先生是从根原之地出发走向通人的学术境界的,分开本原之学,所谓通人也就成了庞杂而无所依归的空洞谈论。先生不仅以本原之学教人,也以本原建设律己。1942年10月22日的《日记》载:
暇念近来读书兴趣日加深厚,此正为道向上之徵,自当爱日以学,稍补往昔怠废之缺。惟根原之地,万不可绝。温经读史,宜严立课程。如幼童时读书现象,方足以致高明广阔之域。(《日记》62页)
先生治学取境高远,气候澎湃,而又渊源有自,淳雅贯通,广而不乱,博而不杂。其根本就是先生在思想上牢牢抓住本来、立足根底,才进入了学术研讨高明光大的博通境界。先生对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清代学者的气候广阔、湛深博通的学术境界充满敬仰之情,在先生看来,清儒的博通正源于根原之地的坚实,所谓“清朝诸大师学问渊博,气候伟岸,其始基率由湛深经术,根原之地所立者厚也。”(《日记》80页)相反,先生在批评古今学人轻浮的学术风气时,往往以“根原之地荒芜”来评判。1944年3月29日先生看到声名显赫的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同治六年正月二十日)记载的常常置于案头“昕夕置案之书”,先生颇不以为然,以为“凡此数十种书,皆非学者根原之地。”先生以为假如分开了根原之地,“循此弗畔,亦徒记丑而博,何能窥寻学问深处。”(《日记》443页)细心研讨李慈铭罗列的一长串所谓案头之书,虽然也是流传广泛造诣精深的研讨性著作,而这里却还缺少的经典文本,别人的研讨终究不能替代本人的学术领会,分开了精熟经典文本的治学正途,就会走上顾炎武剧烈批评学术上的“买铜铸钱”而不是“采铜于山”,最终导致学术本原的荒芜,“而根原之地既绝,则无往而不支离”(《日记》263页)。根原之地是先生一生坚守的学术阵地,其所谓“根原之地”就是以经史为根基的学术涵养、以小学为基础的治学手腕,以儒家思想为原则的精神性情。
人们习惯于将“本原之学”理解为小学的根基与手腕。的确,张先生在治学上十分注重传统小学的根基,湛深经训,仪范许郑,信仰“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的学术信条,但是,先生对本原之学的理解最终还是精神的,是思想的,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精神和品格的坚守。1944年4月7日先生从李一真处借来《复性书院简章》阅览一过,对马一浮“以六艺统摄一切学术”的思想坚信不疑,以为“马氏揭橥之正,足以箴肓起废”(《日记》457页),先生以“六艺之学”统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思想,不仅是简单的学术分类,而是对中国文化根本思想的坚持和保守,这一点我们该当给予足够的注重。先生以为,中国学术虽然包罗宏富、意义广阔,而当以六艺为纲,一以贯之,纲举目张,以经学的思想贯通史学、哲学和文学。在这里,我们特别举出《日记》对《史记》和司马迁的理解以为佐证。一般研讨者都以“长于修史”称赞司马迁,而先生却以“功在传经”理解《史记》。在先生看来,经过秦火之后,司马迁才是最有成就的传经者。这一方面是由于司马迁“嗣其家学”而整理和保存了大量历史典籍和文献,另一方面也由于“自创新体”而坚持和开辟了以六经为代表的文化精神:
虞、夏、商、周《本纪》成,而《尚书》尽在其中。《列国》《世家》成,而《春秋》在其中。《礼》《乐》诸书成,而七十子后学者所记可考。见其大较,非传经而何?《五经》中惟不采《易》《诗》,以二书遭秦火而全也。(《日记》437页)
张先生特别注意到司马迁的传经之功,注意到司马迁对中国文化精神的传承。比起那些皓首穷经的汉代经师,司马迁无论是对经典文本的保存还是对经学精神的发扬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张先生一生著作丰富,涉猎广泛,而其本质是对以“六艺”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坚守,这才是“本原”的根本意义。“本原”不是分开精神、割裂义理的所谓考据和所谓的学问,实际上,先生对那些繁琐细碎缺少精神坚守的考据和厮守一经的所谓学者,根本上是不以为然的甚至是觉得可笑的。《日记》中多次记载先生为学生讲解《西铭教》,先生以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足以为青年“开辟胸心”、“鼓励士气”(《日记》83页),这也是先生不断鞭策本人时时追求的人生目的。
2.“湖南之矿,终待湖南人发掘之”——湖湘的学术传统。
当许多学者都在以所谓阶级斗争思想为理论指点、以农民起义为历史主线研讨所谓中国历史的时分,先生却在冷寂中将研讨的重点转向对中国古典学术精神的寻绎和清代学术流派的思想脉络构成的研讨。他的《郑学丛著》、《顾亭林学记》、《清代扬州学记》、《清儒学记》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先生对清代学术的研讨起步很早,还是在湖南的时分,先生已经构成了“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日记》451页)的杰出见识。先生博通的知识构成、庞大的学术目光,很容易让人疏忽了他学术的湘学传统,其实,先生无论其人,还是其学,都表现着浓重的湖南人的精神性情,先生的学问根植于深厚的湖湘学术土壤。据《日记》记载,先生青年时代在京师游学期间在吴承仕(吴检斋)先生居所与钱玄同先生相遇,谈话间吴检斋对湘籍学者的学问不以为然,以为“湘人言经者,多不明故训,于音理犹茫然”,并忆及当年湘籍学者叶德辉以《六书古微》向章太炎先生讨教,太炎先生笑曰:“此矿区尔,犹待吾为开采而后可用也。”面对江左学者咄咄逼人的言行,年轻气盛的先生颇为不平,遂应声对曰:
“湖南人之矿,终待湖南人发掘。”时钱氏在座,吴顾钱曰:“此其志不在小,可畏也。”相与大笑。(《日记》76页)
“湖南人之矿,终待湖南人发掘”——显示了青年张舜徽对湖湘文化精神价值的认同,也表现了先生一种壮怀剧烈睥睨天下的学术自信。立下这样志向的时分,先生还是弱冠之年,从此而后,“广阔湘学”、“为湘学争地位”,不断是先生为之努力为和奋斗的学术目的。1942年12月17日先生读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为其叙说的曾国藩、罗泽南、胡林翼、刘蓉等湖南先贤的忠烈精神而感染,为湖南人在整个中国近代史有开启风气领袖天下的英雄壮举而骄傲,盛赞“咸同之时,湖湘先生大抵以儒生奋起武略,功勋烂然,为前古所未有”(《日记》217页)。先生为曾国藩、胡林翼、罗泽南为代表的湖湘先贤“好学无斁,不以贫病忧患动其心”的精神所感动,在先生看来:
艰辛卓绝至于如此,乃天地之至文也。具此真学问、真精神,胜于诂字说经者万万,虽无经说,何害湖湘学者之伟绝!……此间共事者多江浙士,亦时时为道及之,俾能明乎湖湘学术之大也。(《日记》219——220页)
虽然先生本人“喜治小学经训”,但他却不以诂字说经为意,以为以天下为己任而奋起行动的“儒效”精神,才是“真学问真精神”。那个夜晚一向冷静理性的先生,不由大方激昂,心潮崎岖,立下承继湖湘先贤踵武,“光大湖湘学术”的宏愿:
广阔湘学,正今日事,黾俛图之,没身而已。
“广阔湘学”,不是少年的一时冲动,而是“没身而已”的终身目的;不是厮守一隅的狭隘的乡党成见,而是对湖湘人投袂而起奋然前行、以天下为己任的忠烈思想的心理认同。先生对湘学是承继,更是发展,因而他才以博大的心胸汲取天下学术的滋养,对吴学、扬学和皖学都作了深入的研讨,且给予极高的评价。
光大湘学的理想,首先源于先生是湖南人,湖湘自然山水和文化传统滋养了先生的精神世界。先生生于湖南沅江,少年时登山临水,获益良多。故土苍茫之湖水、参天之古木,翱翔之雄鹰,熏染着他博大高远的学术志向和刚毅安静的思想品格。在《日记》中,先生时时流显露对屈大夫行吟的绚丽辞章、周敦颐雄阔的理学思想、王夫之博大的通人气候的崇敬之情,这些都成为他日后取法模范的精神导师。
其次,源于学术上湖湘学人对先生的深入影响与真诚协助。先生17岁后负笈远游,遍访通人,而得益于湖湘学者最多。先生晚年撰《湘贤亲炙录》,叙说生平往事,一一胪列对其有重要影响的湘乡长辈,其中包括了余嘉锡、曹典球、孙文昱、杨树达、骆鸿凯、黎锦熙、李肖聃、辛树帜等二十余人,他们对先生影响是深入的,直至晚年,先生亦不曾忘怀,谓“湘中诸老,惠我犹多,以为孺子可教,相与奖掖而诲导之。”1944年10月26日湘中耆儒杨树达先生来函盛邀先生赴湖南大学任教,先生由于“逃亡在外,已历五月。行囊久空,衣物荡尽,一家数口处于啼饥号寒之中”而不得已推托,但是先生依然对杨树达先生的提携奖掖之情而深受感动,随即写下了《复杨遇夫先生书》——“书累六纸,纚纚千六百言”,先生在感激之外,再次提到湖湘学术传统,以为以罗泽南、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湖湘政治家,之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建立丰功伟绩,是由于他们“秉其高尚之志以从事学问,学问素成而后发为事业,其能震烁古今,岂偶尔哉?”(《日记》516——517页)高扬湖湘学术精神,是先生不能忘怀的学术使命。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是先生从心灵深处对湖湘学术传统中的恢弘的精神气候和经世致用的精神品格的敬慕和跟随。
《复杨遇夫书》言:
往在蓝田,与江浙诸友论及有清学术,彼辈盛称考证为吴皖所专,非湖湘所能匹。舜徽则谓楚南诸先正由义理发为事功,足以润饰天地。儒效自此而宏,不言考订何害?彼穷老尽气以考文字说名物者,厕诸罗、胡、曾、左之班,只堪作谈古品艺伎俩耳,何足以知国计民生之大奚与乎?(《日记》517页)
先生一方面学宗许郑,精于考证,由小学入手,开辟经史子集的博学路径,以抗争人们对湘学疏略考据的讥议;而另一方面先生也以为将湖湘学术的真正精神是“由义理发为事功”,是实事求是的学术根基和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的统一。学术终究还是要付诸实践见于事功,而不仅仅是书斋里的名物考据义理钩沉,无论如何,国计民生的现实意义总要大于细琐的名物考据。先生在兰州期间,特别写道“余尝以为今日教士所亟,在乎立志。所谓立志者,非教其徒为著书立说之人也。天地间学者不必多,而切实做事之人断不可少。”(《日记》706页)这样的话,至今读来依然发人警醒。“通经以期致用”——从学问出发,以体国经野,兼济天下,是先生对湖湘学术的深入理解,也是他毕生坚持的学术路线。
正缘于对湖湘乡贤的精神敬慕和对湖湘学术传统的深入认同,先生曾立志写出一部反映追溯湖湘学术源流、探索湖湘学术精神性情的学术研讨著作,但是他的研讨计划很快为另一位著名学者钱基博先生率先完成了。1943年5月4日上午先生拜访同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的钱基博先生,钱基博先生向张先生透露了本人撰写“百年来湖南之学风”的写作计划,“就湘贤事迹叙说之,藉以作厉士气。……但从诸人困心衡虑时论议行事,加以阐扬,以为后人处贫贱患难者之鉴。”英雄所见略同,先生自谓“余旧有志纂《湘贤学案》,迄今不就,竟为此翁所先。”(《日记》422页)钱基博先生的著作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近百年湖南学风》,钱基博先生是张先生从来敬佩的学者,对钱先生的著作,张先生一方面为其“所见之同”而欣喜,另一方面也有“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某些遗憾。后来先生在《清儒学记》中虽然还是撰写了《湖南学记》一章,但可以肯定不是早期规划中的“湘贤学案”的气候和规模了。
3.“学归致用,而儒效乃宏”——实用的学术理念
先生一生是在书斋中度过的,但是先生一点也不满足于坐而论道、袖手谈论的雍容清雅,而是强调一个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还是“通经致用”,先生的学术理念是入世的、切近的、实用的,而不是出世的、缥缈的、逍遥的。“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这种自屈原以来,根植于湖湘文化传统中的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建功立业的忧患认识,也时时出如今先生日记中。刚过而立之年的先生在《日记》中写道:
自念年已过立,百无一成,倘不及是时于役四方,终恐闻睹日隘,无所建树于当世。稽之礼典,古之士大夫致仕而后归教于其乡,老不教导谓之无业之人。然则收朋勤诲固艾耆以后之事,奚必以有用之岁月,尽瘁于口讲指画耶?(《日记》341页)
简单的书斋生活几乎构成了先生的一生,而他真正的理想却不限于此。对于讲堂上“口讲指画”和孤灯黄卷中的“手批口吟”,先生也流显露一丝的厌倦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日记》真实地展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立言”与“立功”面前的精神困惑和心理矛盾。他不屑于“以有用之岁月尽瘁于口讲指画”,而执着于“由义理发为事功”运营天下的湘学传统,又无法找到完成其兼济天下建功立业的理想道路,这就构成了心灵世界的孤单和精神深处的矛盾。一方面他在学术领域勤奋著述,坚守文化阵地,另一方面他又有激烈的事功观念,有兼济天下的政治胸怀,不满足于象牙塔里的高头讲章,而是强调“文之为用,至为宏远”(《日记》650页)。先生以为“古人著书率出于不得已,今人著书皆可已而不已”(《日记》719),在先生看来,“著书”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学问的终极目的还是责任,是担当,是行动。任何气壮山河的谈论都不能与经天纬地的事业相比。支撑先生“通经致用”思想的是传统儒家一贯强调的“儒效”理论。在“言”与“行”的关系上,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坚持“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的主张,以为“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而深切著明也”,力践躬行的思想对张舜徽先生的影响是深入的,因而他常以《礼记·儒行》、《荀子·儒效》教诲学生,正由于这里强调的是儒家立言为公行之天下的思想: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 (《礼记·儒行》)
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夫是之谓中事。
(《荀子·儒效》)
原始儒家不断力图以切实的行动主张矫正将儒家理解为纵横谈论无益于事的非议,“夙夜强学以待问”,勤学的目的在于力行,建立周公式的“美政美俗”的“大儒之效”才是儒家的真正理想。顾炎武对“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的空谈极为反感,以为所谓明心见性的空洞谈论直接导致了“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社会动乱的严重后果。而真正的儒学是面向社会、面向人生,注重行事的,因而顾炎武确立了“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三》)的学术理想。有响斯应,孔子、荀子、顾炎武等伟大思想家经世致用的思想对先生产生了深入的影响,成为先生学术思想的重要原则。1942年10月19日先生“闭户读彭定求《南畇文稿》”,彭定求竭力倡导“孳孳以躬行是尚”的原始儒家精神,剧烈批判近世以来“支离于训古,沉溺于词章”的浮泛清艳的学术风气,以为这是“求儒于言而不求儒于行”,是对儒家精神的根本背离,先生深以为然,充满感情地写道:
透辟精切,洞照数千年来士子症结矣。(《日记》53页)
将学术从背离现实的空洞谈论调整到关注苍生的切实行动,是先生几十年来学术努力的方向。正由于对经世致用学术思想的坚持,先生反对一切没有根基的浮泛谈论,尤其是反对志气萎靡、销蚀风骨的所谓辞章,先生自壮岁讲学上庠,弟子三千,而入先生门下总听到先生“少读诗词,多看有用之书”的教导,先生耻为文人,不屑于诗词创作,就在于他深入地了解古典诗人感伤脆弱的情感世界,而一旦浸染此种习气,就意志消磨练当重担:
盖士子自能识字即吟哦于五言七言,诵习愁苦之词既多且久,则志气日就靡弱,不能自拔于流俗,由是文士日多,而真才日少。(《日记》267页)
先生的阐述让我们想起了柏拉图《理想国》中对诗人的驱赶令,而驱赶诗人的根本缘由是柏拉图以为甘言蜜语的诗人是消解人们意志的,是感伤的、缺乏力量的。虽然先生的意见不免有个人的偏好,但是诗人过度的感伤的确是有碍志气恢宏,最终有碍于行动和功业的建立,所以先生不断告诫青年不要以“少年有用之身,半消磨于无病呻吟之地”。先生年少时就喜读《曾文正公文集》,“至今而无厌,弥研绎弥觉有新理焉”(《日记》247页),先生理解的曾国藩是“窥见古人大体大用”的,是“归宿于礼以经世”的,先生理解的学术是“学归致用,而儒效乃宏”(《日记》276页)。
4.“尊德性、道问学不能分做两件事”——通人的学术气候
先生一生以“博通群经,不守章句”的通人自期,反对厮守一经一家的声气结纳,反对支离细碎的名物考据,反对消磨意志的辞章吟哦。学者对于先生通人之学多有阐述,但结合先生《日记》,我们应该强调的是,先生的通人境界不是简单的博通四部,而是道用一体知行合一古今通贯的学术理念。张先生在北平民国学院为学生讲解《中庸》的时分,特别指出:“尊德性、道问学不能分做两件事”(《日记》416页),在先生看来,真正的通人不仅仅是知识的广博而是胸襟的开阔、志气的恢宏,是知识与道德的融为一体。
“通人之学”首先是胸怀天下、志气恢宏的博大气候。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凡有学生请益,先生必告之以立志高远为先:
二千年之间其能顶天立地以天下自任者,率由立志不同于常人,能自拔于流俗耳。(《日记》515页)
夜间樊生、赵生来请以读书之要,余谆谆告以立志远大不可拘于小近诸语。(《日记》715页)
每论及志向,先生就热情迸发,气势澎湃,《日记》载先生在湖南时的一次演讲充满热情地说道:“观古今顶天立地建不朽之业于万世者,大抵以泰山为笔,东海为池,大地为纸,事业为文章”(《日记》477页),这志向不仅仅是文章学术,也是道德事业,不仅是立言,更是立德立功,依先生的理解,建功立业是更大的学问更大的文章。先生以学术行世,志向却不局限于学术,先生甚至不像一般学者那样不屑于政治,而是强调社会担当,以天下自任,以为“不以仕为贤,自周以前无之”(《日记》276页),他厌恶庸俗的政客,却推举伟大的政治家。无论是“道”还是“学”,都是广泛的,先生教诲青年与其一味地愤世嫉俗悲天悯人,不如投袂而起,力挽狂澜,以建立顶天立地不朽之功业为己任。
其次是融汇古今贯通四部的知识视野。先生治学以博通为悬的,强调立足经史,会通古今贯通四部。钱钟书先生“打通”的学术理念,侧重的是中西文化之间的沟通融合,而先生的“会通”则更侧重古今之间的历史联系。对于固于一隅“拘狭地守着经史子集的旧圈子,不肯摆开,此疆彼界,各有范围”的经生学究式学术,先生历来是批判的。先生以为乾嘉学术之病,就是学术的支离,“乾嘉以后,清学乃由极盛而衰,士子不达于为学之本,群趋支离破碎而不知返”(《日记》107页),支离与割裂是先生对乾嘉以来学术之病的科学诊断,正由于如此,先生才标举会通,以经史子集的贯通以矫正学术流弊。
第三是卓尔不群、目光独具的学术见解。在学术之外,先生也常常将目光转移到人生、社会、教育、军事等广泛的方面,谈论风生,多有创获,表现出一代学术通人卓尔不群的思想风采。《日记》中先生对“西北开发”、“厚禄养廉”、“以立志治兵”、“人才兴国”等问题多有谈论,其见解都立足学术根基,因而富有启发意义。先生本人是教师,但先生坚决反对立门户、开宗派。先生主张圣贤师法天地,师法古今,师法自然,师法一切可师法的事物,而不厮守“一先生之言”:
余尝以为五伦中无师弟,只当属之朋友之列。求师之宜,赓以交友之宜。博师不可遽得,即以古人为师。亦奚必守一先生之言自以为是乎?(《日记》696页)
先生以为,在中国以“五伦”为基础的伦理关系中没有师生一伦,师生之间只是学术商讨的朋友。先生以为以师生之谊行宗派之实,是祸国殃民之阶。1942年11月5日,先生与钱基博先生有一次谈话,钱基博对明代东林党人的“声气结纳以为标榜,党同伐异以为把持”,深表气愤,以为:
武人跋扈,文人何尝不跋扈?而矜意气,张门户,以庠序为城社,以台谏为帮凶。恩怨之私,及于沙场;不恤坏我长城,以启戎心;国事愈坏,虚誉方隆,而东林讲学,实阶之厉。(《日记》101页)
钱基博先生与东林党的代表人物顾宪成是无锡同乡,先生对钱基博“不以乡曲之私而阿其所好”的公正见识深表称许。先生与钱基博先生一样立言为公,以学术为根基,目光远大,气候博通,故其见识超迈群论,影响深远。
更应注意的是,先生的“通人之学”,是有所本的,是立足于本原之学的,是切近于国计民生的的,是植根于湘学传统的。尤其是湘学精神对先生通人之学的境界影响是深远的,先生晚年为罗焌《诸子学述》重印所作序言中说:“湘学先正之学,以经史根其基,而旁及诸子百家,规模浩大,与江浙异趣”,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先生的通人境界是“植根经史,而旁及百家”具有湖湘文化精神的“通人境界”。假如分开了先生的学术坚守而奢谈先生的“通人之学”,势必将先生的博通引入庞杂而无所依归的境地。《日记》阐述“致广阔而尽精微”一句,先生谓:
致广阔而不尽精微,则有肤泛之弊;尽精微而不致广阔,则有偏狭之弊。极高明而不道中庸,则有诡僻之弊;道中庸而不极高明,则有汙邪之弊。
三、论学以见识第一,以器识为先
先生论学以见识第一,以器识为先。《日记》引《宋史》刘忠肃言:“士当以器识为先,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也。”先生不屑于文士们的浅吟低唱,也对乾嘉以来诸儒细琐的名物考证不以为然,而强调学术的社会责任,是对学术、对人生、对社会、对自然的全面理解。与一般日记日常琐碎的生活记载不同,先生的《日记》更多地记载了他对社会对人生尤其是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理解,这些理解对我们极具启发意义。
总体上说,先生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在“五·四”以来社会与文化剧烈变革的潮流里,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传统文化及其精神价值本质上是认同的,即便批判,其态度也是温和的、建设性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可能缺少新文化倡导者血脉贲张的革命热情,缺少对传统文化某些负面效应的批判认识,但是在整个社会都卷入批判传统的潮流的时分,他们却坚守传统文化的阵地,竭力为传统文化保留住一点什么,坚守住一点什么,保证了中国文化精神薪火相传,其文化传承意义是不容否定的。王国维、章太炎、吴宓、陈寅恪、梁漱溟、马一浮、钱基博、钱穆等本质上都有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他们主张对传统文化应有“了解之同情”,而不是一味否定、一味批判,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先生与文化保守主义者精神上是相通的。
经学存废是五四以来文化界争论的重要问题,一方面是吴宓、梁漱溟等文化保守主义者“倡导读经以作新民德”,另一方面是以胡适、鲁迅、傅斯年为代表的新文化的倡导者们“不读线装书”的激烈呼唤。这样的思潮也影响到先生执教的校园,针对胡适、傅斯年对经学的激烈批判,先生《日记》中大方陈词:
余尝以为吾华有史已数千年,往哲垂诸简册而可宝者,在乎为人群立准绳。换言之,即阐明处事接物之原理、原则也。《四库提要》有云,经者非他,天下之公理而已。公理云者,犹算学中之定理公式,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者也。夫学者所事端在穷理,穷理之范畴又有人理、事理、物理三者之辨。今人趋重于声光化电之学,特物理耳。研精物理,自有其一定之公理,足以执简驭繁。若夫为人临事之公理,则存诸古籍中者实大且多。使人不欲明于人理、事理则已,如欲知之,则古代经传实有诵习之价值,而不容屏绝之。(《日记》346页——347页)
先生以为古代经学是中华数千年文明的承载者,包含着华夏民族仁理忠信等基本伦理思想,而这恰恰是传统经学的精神价值所在,不仅不该当废止而且是应该大力弘扬的。虽然社会政治剧烈变化,但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思想体系、伦理系统却具有历史的承继性和结构的稳定性,不能随意改变。经学的存废实质上是中华文明的存废问题,是传统道德的存废的问题,因而先生的立场是旗帜鲜明的——“古代经传实有诵习之价值,而不容屏绝之。”在物欲横流、人文精神失落的今天,回想先生在抗战烽火中的阐述,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虽然先生对古典经传也主张“有所别择而不可拘泥”,但是这种选择,一是删繁就简,讲求精粹;一是去虚就实,讲求功效,而对经典的精神实质先生是认同的、理解的、充满崇敬之情的。
对经学的态度,触及到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评价孔子。先生不满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人“非孝废孔”的言行,坚定地维护孔子仁孝的思想学说,先生以为孔子思想是维系社会稳定的精神系统,非孔的结果最终必然导致社会的动乱:“不及十年,每每大乱”。《日记》谓:
夫孔子生于周末,去今二千四百余年。其所论说,容有益于古而不适于今者。且人事日新,文明日进,而吾华立国之道求之孔氏而足,是固拘虚之见也。虽然立国于大地,必有其所以维系人心于不敝者。孔氏于既往二千年中,为天下纲纪,足以济刑政之所不及者,实大且多。今欲有所革易,自必先立一伦理之中心思想而后可。譬诸窭人之子今渐富矣,恶夫茅茨采椽之陋,必别营峻宇雕墙而后可徙也。若未及其庐之成,遽火其故居,则必彷徨无以安朝夕,故言废孔可也,废孔而不别图树立伦理之中心思想不可也。(《日记》370页——371页)
文化是一个缓慢演进的历史过程,文化的变革也该当是循序渐进的,因而先生反对文化的突变,反对剧烈的文化革命。无疑,先生也以为在社会与文明不断提高的现代,厮守孔子学说,以孔子思想为立国之本,是“拘虚之见”。而他同时也以为,破坏该当以建设为前提,解构必须以建构为基础,正像我们要拆除一个旧房子,一定是以建设新房子为前提的。在新的伦理思想还不成熟的状况下,就匆匆破坏了维系中华两千年文明发展的孔子的思想大厦,势必演化为伦理的崩毁和道德的衰微。新的道德的建设必须在历史承继的基础上才能完成,没有历史渊源没有文化承继的所谓思想创新,终究是没有基础的空中楼阁,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在阐释爱国主义思想的时分,先生以传统文化的“孝”的观念与现代爱国主义精神相嫁接,提出了“爱国自孝其亲始”、“不爱其亲,而忠于国者无之”(《日记》372页)的重要观点,完成了现代思想与传统道德的互相联系互相沟通。
《日记》是零散的断续的,却呈现了先生学术与哲学思想的整体性一贯性。对于古史辨派对古典文献的轻率怀疑和主观臆断,先生深表痛恶。疑古之风的弊端首先在于对待历史文献的轻率行为,“自疑古之说日昌,学者未开卷,即疑古人无是书,古人不能作是书。闲坐游谈而不读书,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日记》522页)
一定程度保持对传统文化的怀疑精神并不错误,但是将怀疑当成一种理论、一种观念或一种出发点就偏离了学术的方向,而演化成游谈无根的主观揣度。在这里,先生倡导的依然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不是对怀疑精神的否定。
其次,疑古之风的要害在于割裂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基础,悠久绵长的中国文化历史由于缺少了古典文献支持,而变成了近于虚无缥缈的传说:
今之考古史者,知人论世,于此独详。迨求之不得,一概目为无稽,非特不信炎黄实有其人,且疑大禹非圆顶方趾。有史之期,断自殷周,乃不啻自缩其历史至数千年矣。(《日记》368页)
疑古形成的遗害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古典学术,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自信,疑古的结果是历史虚无主义的盛行,悠久的华夏文明不得不拘谨于狭小的时空里,显得贫弱而惨白。
因而先生对待历史的态度是以“释古”替代“疑古”,主张在历史文献的基础上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意蕴。先生的释古思想是在阐释经典中构成的,《日记》记载先生在课堂上,“为诸生讲《大学》毕,因纵论宋贤改经之失补课训”,特别提出了“释经可也,改经不可也”(《日记》329页)的重要观点。以对经学的阐释替代经学的臆断,这样的思想扩充开来就是以释古替代疑古,越来越多的地下文物的发掘有力地论证了先生释古思想的提高意义。
正由于先生在经典文献的基础上对古代经典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剖析,所以才在阐释传统文化思想上获得了重要成绩。这在《日记》中,多有反映。1943年4月19日至5月2日,先生在蓝田任教时为学生讲习《中庸》,先生对本人关于《中庸》意蕴的发掘十分注重,因而不惜笔墨,六次记载了讲解《中庸》的详细内容。《中庸》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其内容触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关于社会、人生、自然、心性、道德、学习等广泛内容,先生正是通过对《中庸》的全面阐释而抒发本人的哲学考虑的,换言之,对《中庸》讲述表现着先生本人的人生与哲学考虑,是先生哲学思想的重要文献,因此,《中庸》讲疏中的重要的思想是不可疏忽的。先生《讲疏》的精义表现在如下几点:
第一,以“生”释“性”,由于自然生命的质朴引出后天的教化。以“耐”释“能”,将思想的阐发建立在科学考据的基础上。
第二,打通文献,以《吕氏春秋·知分》“安分”思想解释《中庸》“素其位而行”,强调在荣辱穷通之间安命顺时、从容淡定的君子胸怀。
第三,以礼释孝,剖析丧礼构成的历史,强调礼是文化属性,也是自然属性。以为人类的仁爱之心,始于事亲,典章制度可以变化,而精神本质却不能变化。
第四,从剖析“君臣”之义入手,剖析“五伦”构成的文化意义,强调社会秩序的稳定。
第五,以道用一体为思想基础,强调“尊德性、道问学不能分作两件事”,以为儒家思想中的广阔与精微、高明与中庸其本质上都是一体的。
第六,剖析“温故知新”的意义,指出“新”不仅仅是知识之“新”,而是时代之新,是“时务之新”。阐明孔子强调温故知新的意义是矫正俗儒“知古而不通今,胶柱鼓瑟而不知合变”的偏狭孤陋。
在传统思想的研讨中,先生是富有创新认识的,即便是寻常的历史文献,也显示出他不同常人的深入见解,“《中庸》六论”代表着先生学术思想的成熟,从这里我们更可以看到《壮议轩日记》出版的重要学术价值。
四、日记是其个人心志与情感的流露
《日记》的另一个意义是先生个人心志与情感的流露。先生是学者,孜孜于学术,但同时他也像普通人一样在世俗世界里生存,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日记》中的先生,时而志气恢宏,时而黯然神伤;时而为学术所得而喜不自禁,时而又为生计困难而愁眉不展,这让我们在学术之外看到了一个性情饱满、感情丰富、兴趣良多的学者的心灵世界。《日记》中特别感人的先生是对父母的怀念,《日记》起笔时先生的父母均已辞世多年,而每至父母忌日或是冥诞,都唤起先生无限怀念之情。1943年1月9日(农历十二月初四)《日记》载:
今日为先公忌日,怆然伤怀。回忆儿时,侍父读书山中,现象历历在目。椿庭弃养,忽忽十有四年;慈母见背,亦已三载。世乃有无父无母之人,鲜民之哀,曷其有极。自丁丧乱,忧患迍邅,戚戚无生人之欢,每当孤灯兀坐,四顾惘惘,百愁猥集,万念都灰。而昔日侍亲之情状与吾亲所以爱我之殷切,常萦回于吾心。缅怀音容,如侍其左右,至涕下不能止。(《日记》279页)
这是先生的一则日记,也是一篇情思低回哀婉痛切的留念文章。万籁俱寂,孤灯夜坐,先生仿佛又回到儿时侍奉父亲读书的时光,回到了慈祥的母亲身边,不由得悲从中来,泪眼婆娑。1942年12月11日《日记》记“昨夜梦侍先母于庭,诲我谆谆”,这幅慈母梦中谆谆教导的图画,让我们感到先生对母亲的怀念之深。先生对父母的深切怀念,决定了他“以孝立身”“爱国自孝亲始”等思想的构成,抽象的思想总联系着丰富的情感世界。
先生不仅留念本人的父母,也留念心目中的文化导师。1942年10月24日(农历9月15日)的《日记》写道:
是日为朱子冥诞,心香一瓣,惟默祝而已。(《日记》75页)
怀念朱熹的一瓣心香,不仅仅表现先生对朱熹的敬慕,更是对整个文化的尊崇,只有先生可以想到为一代理学大师举行如此严肃的一个人的留念典礼。
《日记》中有先生青灯黄卷的苦读形象,也偶尔有一时的天姿纵逸,流显露先生性格的自然天真。《日记》记1942年11月20日先生在张汝舟处饮酒:
晡时赴张汝舟酌。汝舟奉佛持戒以蔬食宴宾,且有旨酒,余饮独多,微醺。归时,月色皎朗。与共事数人行松林中,便道访宗霍先生,畅谈至更初还院。(《日记》152页)
先生勾勒的饮酒归来图,语词俭省,笔墨洗练,仿佛是一幅白描丹青,将明月松间微醺归来的意境清晰地描画出来。先生有小酌的雅好,《日记》中每每有“某君招饮,座中八九人,余饮独多,醺醺欲倒,幸不及乱”的记载,微醺之后,先生也多次有“后当戒之”的自责,但似乎也没有改正,而正由于没有改正,则更多了几分可爱、几分单纯。
先生一生耻为文人,不以文辞为然,但这并不是先生拙于文辞。恰恰相反,先生文笔凝练,风格刚毅,叙说简约流利,从不拖泥带水,叙事状物、写景抒情都极具特色,构成了文白兼具、雅正通脱的“舜徽体。”
先生在紧张的学术研讨之余尤喜郊游,而郊游所历,一经先生记述,往往就成了魅力独具的优美散文。例如:
朝食后,高生、王生来谈时许,旋侍余往游狮子山,去此十里而近。余已月余不涉足郊野,偶步原隰,心神怡旷。便道过大簏中学,访谢德风;又至精练学校,访徐希靖,欲挽共登此山,皆不遇,乃与两生上至其巅。山虽不高,而岩石甚奇,树木从石罅中怒生,有大者,可数人合抱。半山有僧舍,曰隐龙庵,尤清雅,令人留连不忍去。
余彷徨移时,忆及两年前与澧阳孙海航、临澧张云门共登天门绝顶,信宿古寺中,观云海而还。其时亦值春暮,所见景物略与此同。尝于昧爽立龙头岩,以俟日出。下则岩高万仞,余与海航、云门相互依倚,坐诵《洪范》、《中庸》诸篇,生平游乐无逾于斯。自去大庸,两君亦不知萍浮何所,今登斯山,不胜复古伤离之感。
下山时,日已倾昳,与两生买食野店而还。(《日记》362页——363页)
假如不是从先生《日记》中摘录出来,谁会相信这是先生不经意的生活记录。先生的叙说,心绪万千而从容不迫,章法整齐而意脉婉转,从蓝田的狮子山起笔,转入对大庸天门山的回忆,现实与往昔互相辉映,状物与抒怀融为一体。以记游开始,以忆旧收篇,情感上最初是“偶步原隰,心神怡旷”的欣然自得,收篇时则是“不胜复古伤离”的神情黯然,构成了跌宕崎岖、低回往复的艺术效果。尤其是三两青年站在张家界天门山巅朗朗诵读《洪范》、《中庸》的情景,云海茫茫,长风浩荡,高山之巅,书声琅琅,如此雄阔境界给人以激烈的心灵震撼,焕发出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读先生的游记,不由想起了柳宗元、归有光的精心创作的记游记事的优美散文,先生的不经心不刻意与之有相通之妙。也正是由于这样恬淡的心境,使得整个文章表现出朴素自然生动清爽的艺术效果。此外,先生尚有“兀坐浩然思乡”“围炉絮话家常”等生活场景的描绘,也都意趣生动,颇耐寻味。
在修身问题上,儒家不断强调自警自省,在道德上不是外求于人,而是审视内心,厚责于己,薄责于人,因而《论语》有了“吾日三省吾身”(《学而》)“ 见不贤而自省焉”(《里仁》)“ 内省不疚”(《颜渊》)的谆谆告诫。《日记》中记载,在漫漫长夜里先生常常深入地分析本人,充满了传统儒家的自省认识。先生学贯古今,旁通四部,自然睥睨天下,心雄万丈,正由于如此,先生也自省“病根在一骄字”(《日记》336页),对此先生对本人的分析是深入的,仔细的,有时甚至是严峻的:
遐思近来一言一动全未检束,处处觉有骄溢气,开口便臧否人物,最是恶道。此后宜切实自书本外,在身心上作一番功夫。老氏戒仲尼所谓“四去”者,正吾对症大药也。(《日记》31页)
老子当初谆谆教诲孔子的“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成了先生解剖本人疗救心灵的“大药”,先生言行举止都师法古人,自成高格,正由于有了如此深入的心灵解剖,其学术和人格境界足以榜样后人润饰天地。
捧读先生《日记》,不由想起《礼记·学记》的一段话:“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先生生前常常为别人题写这段警句,以鼓励后学。其实,这也是他本人学术与人生的写照。先生一生浸淫学术,志向于此,涵养于此,起居于此,优游于此,一任风云变幻,一直不改以学术为生命雄伟志向,兀兀恒年,终有于成,最终成就他一代通儒和国学大师的辉煌事业。《日记》记录的虽然只是先生学术历史的一个阶段,但其中却跃动着先生与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影,他们在动乱艰辛的岁月里薪火相传、担当使命,其愈挫愈奋的文化精神对我们的影响是深入的,让我们感遭到中国文化不可降服的力量。
-
 支付宝
支付宝
-
 微信
微信

 卫国君主卫灵公天寒凿池的故事 卫灵公墓在哪
卫国君主卫灵公天寒凿池的故事 卫灵公墓在哪 大熊猫和小熊猫有啥关系?她们之间是近亲吗?
大熊猫和小熊猫有啥关系?她们之间是近亲吗? 刘禅才是三国最牛x的人
刘禅才是三国最牛x的人 中国历史上的残暴皇帝:酒后不但羞辱母亲还暴打丈母娘!
中国历史上的残暴皇帝:酒后不但羞辱母亲还暴打丈母娘! 蒙恬的妻子是笔祖娘娘吗 蒙恬与妻子的爱情故事
蒙恬的妻子是笔祖娘娘吗 蒙恬与妻子的爱情故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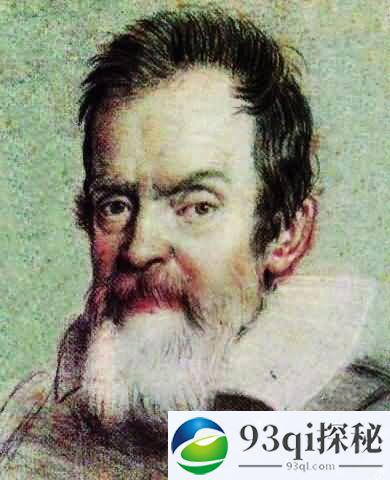 伽利略的遭遇 伽利略亚里士多德有何关系
伽利略的遭遇 伽利略亚里士多德有何关系 慈禧6天扳倒权臣肃顺的五个秘密武器?
慈禧6天扳倒权臣肃顺的五个秘密武器? 春秋时代另类阅兵:国君取悦美女
春秋时代另类阅兵:国君取悦美女